凌晨三点,浙大实验楼又跳下去一个博导
凌晨三点,浙大实验楼又跳下去一个博导。
35岁的杜某某,刚改完第四份基金申请书。
监控里人影一闪,走廊尽头只剩空荡。
 35岁的杜某某在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顶级高校做过博士后,在国内某高校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科研“大神”,大神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刚改完第四份基金申请书,就接到了写第五份的任务。
35岁的杜某某在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在美国顶级高校做过博士后,在国内某高校被外界普遍认为是科研“大神”,大神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刚改完第四份基金申请书,就接到了写第五份的任务。
杜某某这不是个例,一个月内,已经有两名高校教师自sha了。
高校教师的压力有多大?他们每周只要上课就行了?不,他们还要指导学生,还要填表报销,还要申请基金……
高校教师,每年申请的基金项目十个,但能中一项就不错了,每年都要填大量基金申请书的教师,实在是很痛苦的事,但不填又不行,因为考核要求就是这样!
而杜某某只有11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六年的考核。
高校心理咨询中心,排队三个月才能见到心理老师。
看到这些,是不是觉得杜某某很可悲,但在外界看来,这些都是他该做的,是他享受的“高压”下的“高产”工作。
作为教师,工作量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看不到希望,比如,基金申请十投仅中一投,这种绝望会让人心力交瘁。
高校教师普遍承受巨大压力,需频繁申请基金、指导学生、处理行政事务,而项目成功率极低,心理援助资源紧张。每月多名教师轻生,反映科研生态亟待改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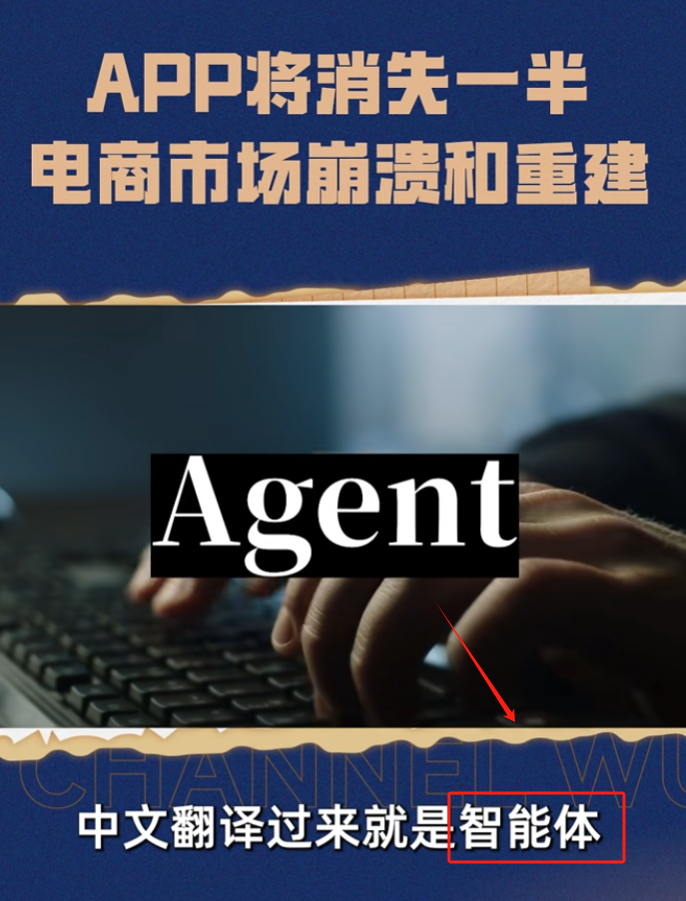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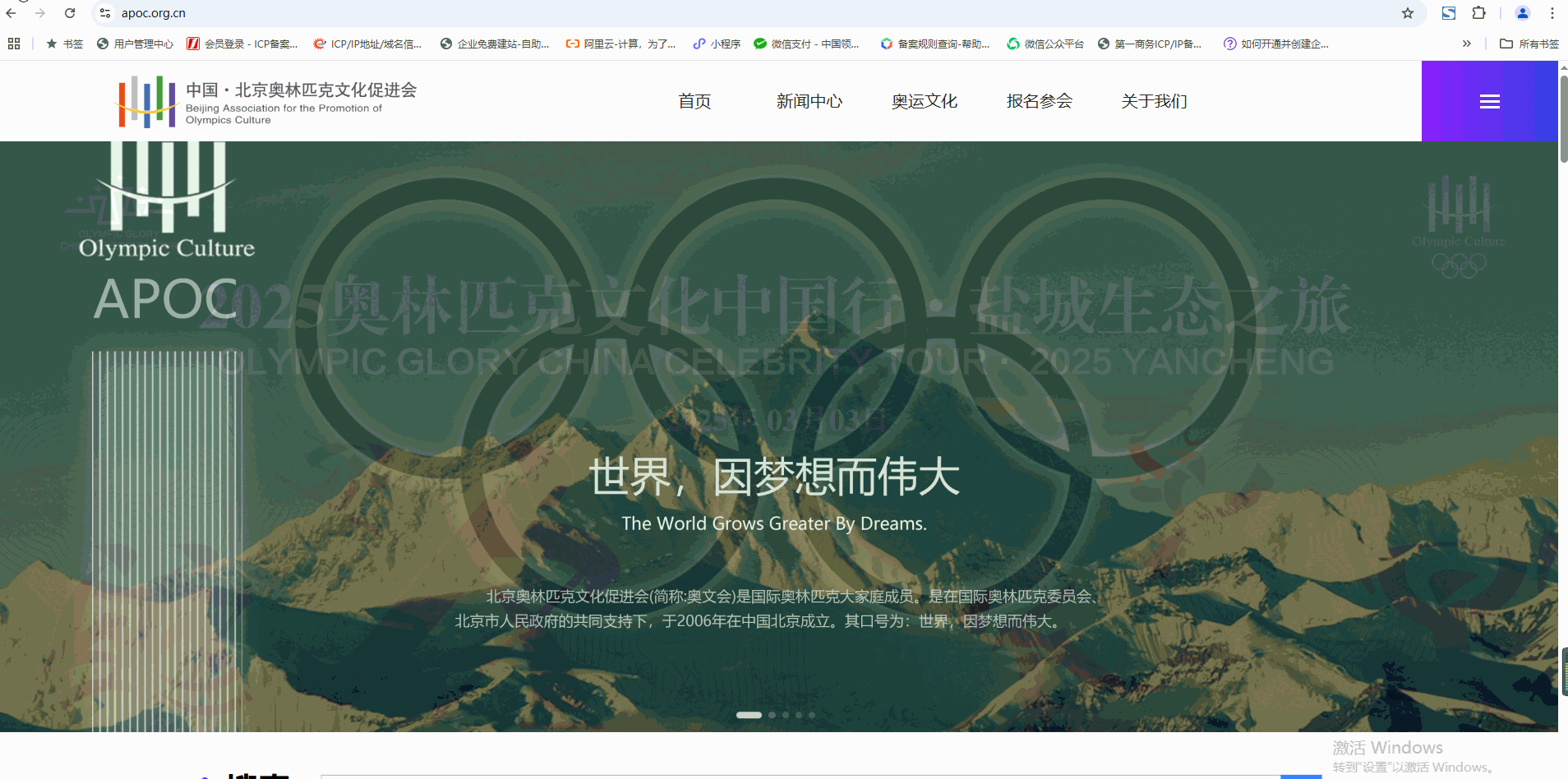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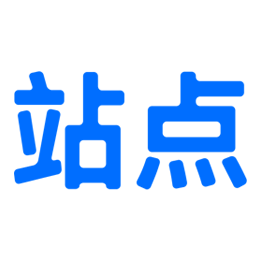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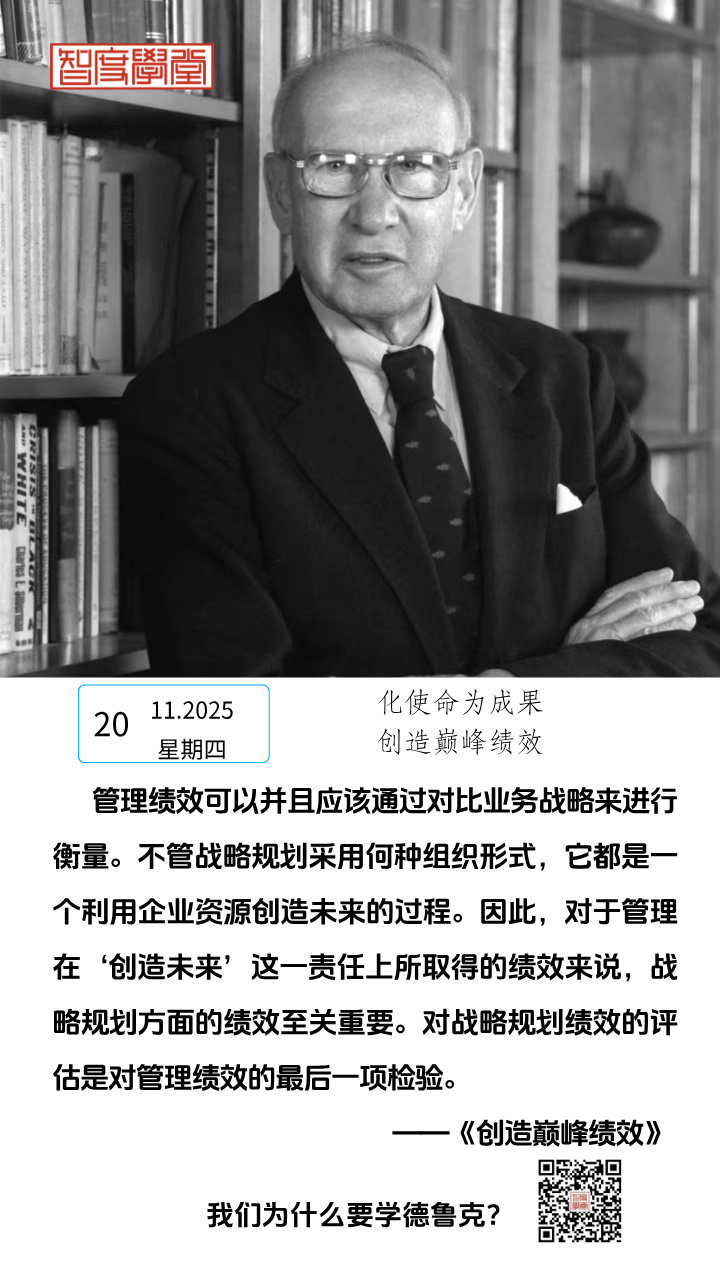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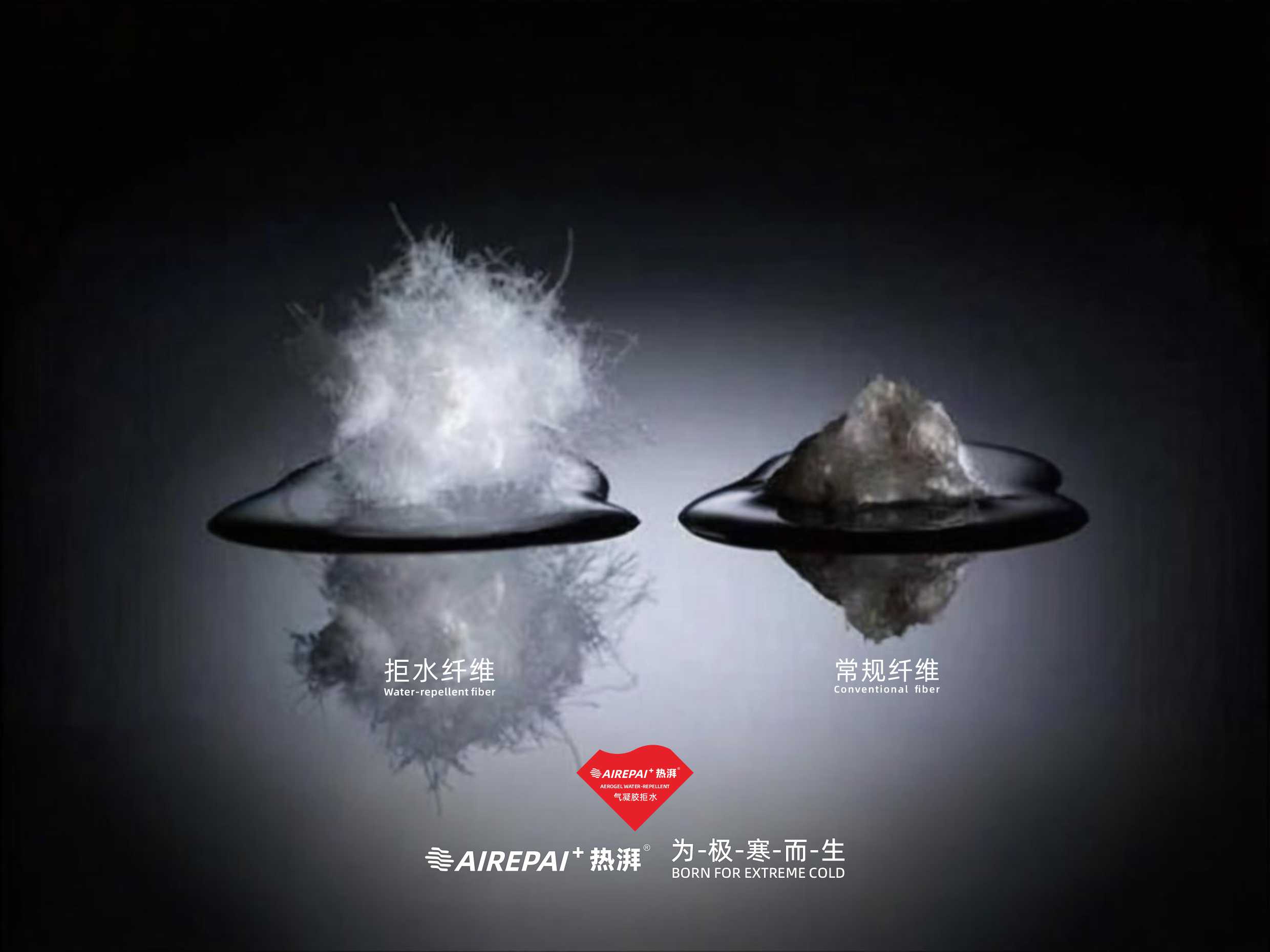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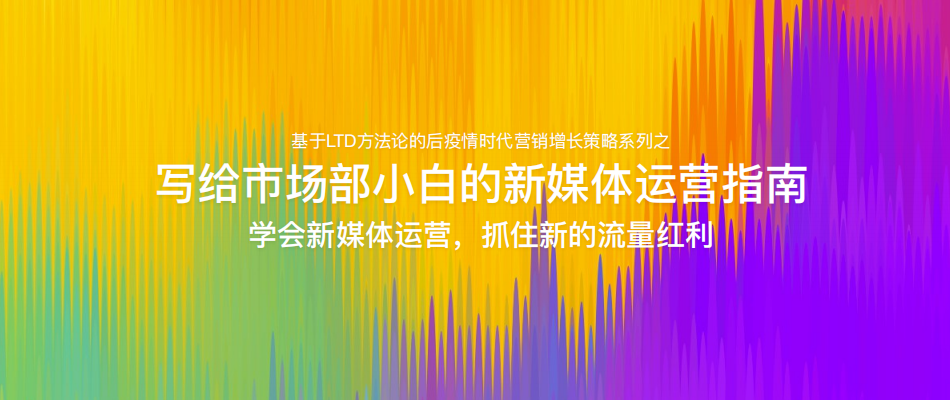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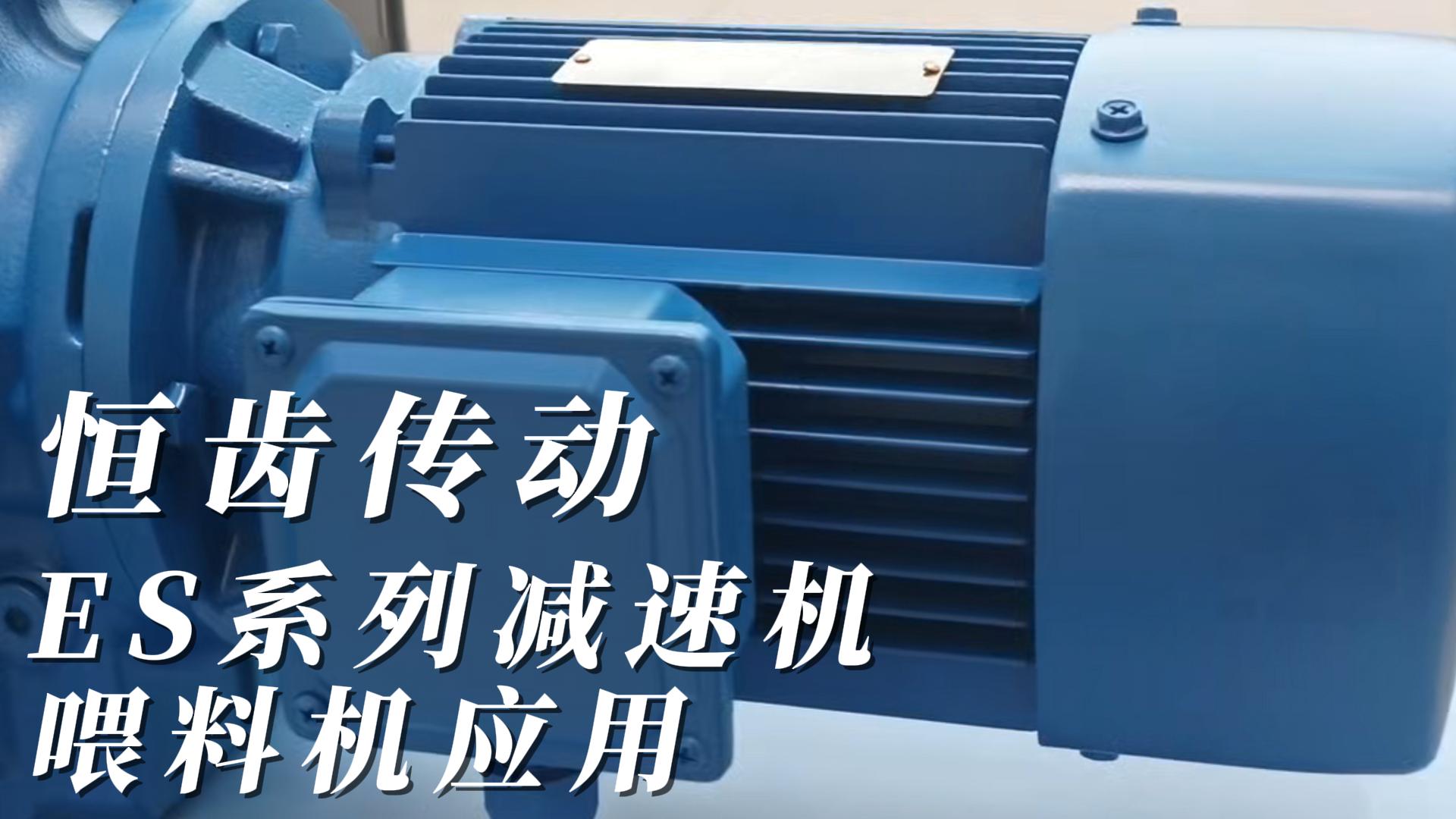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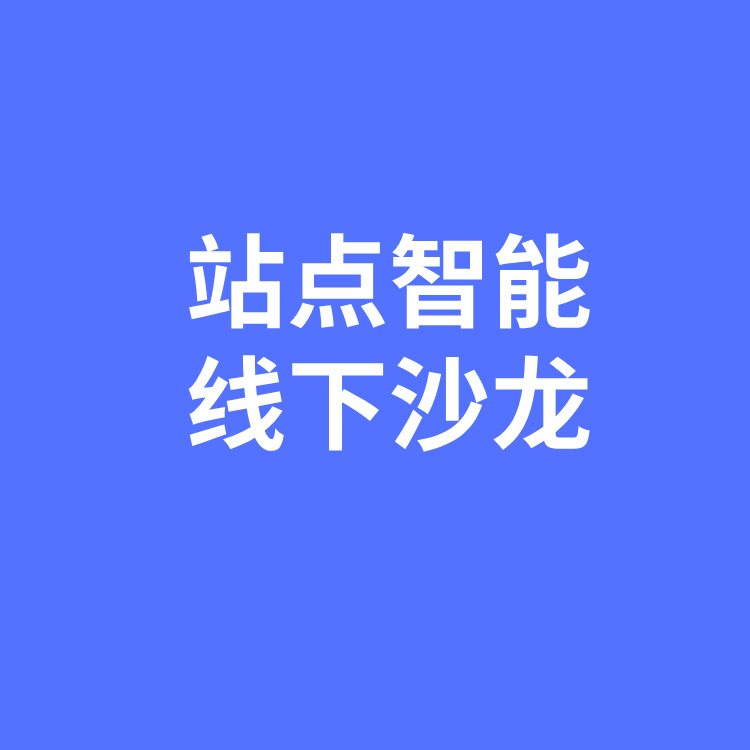











请先 登录后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