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经济增长的根基在于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
【本心推荐】:本文转自公众号中关村产业升级研究院。原题为《自由何价?——悼念米尔顿·弗里德曼》,刊登于2006年11月28日《经济观察报》。周其仁: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1991年秋就读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习,后获其经济学博士学位。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
是的,必须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因为是普遍的自由,所以这“自由”就以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为边界。这样的自由,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并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但绝不主张“无政府”。
——周其仁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经济增长的根基在于普遍的自由,
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
周其仁 | 文
喜欢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各有各的理由。我的理由是这样的,在根本不知他老人家为何方神圣的年代,自己亲身观察和体验过的经济生活,就奠定了接受弗里德曼毕生所阐释的经济法则的基础。这条“米尔顿法则”只有一句话:普遍的自由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
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中,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学校请来北京一位大学老师做报告,讲题是参加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清”——的见闻和体会。不是初中生都听得懂的题材,但有一个“场景”我却记住了:他所去的一个村子,老乡穷得叫人不敢相信——工作队员带下乡的一面梳头用的小镜子,全村谁也没有见过,居然围观起来,视为宝物!
也许就是记忆中的这么一点,让我后来自觉自愿报名下乡。那是1968年,“文革”搞不下去了,而国民经济根本吸纳不了那么多年轻人就业。好在毛主席有办法,一句“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就把上千万知青打发下去了。不过当年我是衷心拥护下乡政策的,报了名还怕不被批准,和十几位同学划破了指头签名给工宣队“上书”,真的一脑门子要去缩小城乡差别。
下乡的地方是王震将军创办的黑龙江农场。适逢中苏关系紧张,农场所在的虎林县珍宝岛当年有过一战。因此黑龙江农场列入军垦系列,其实不过就是发了一身军服种地。由于每月有固定薪水,农场职工生活还过得去,不过有孩子的家庭日子就过得非常紧巴。半年后我被发配到完达山打猎,周遭星星点点有人民公社的村子和居民,才让我看到真正的中国农民,他们干一年活也见不到几文现钱,有的还倒挂公社的钱粮,不少人家达不到温饱——真要有梳头镜子可供围观,还算日复一日单调生活里的一丝浪漫哩!
知青下乡当然要接受再教育。不过我连一位样板戏式的“贫下中农”也没有遇到过。老乡们很朴实,尽力帮教我们这些城里人适应农村的生活和生产。不过我很快发现,他们在公家的大田里的劳动状况,与下班后在自家自留地里的劳动状况,完全不一样。黑龙江的10月,天气已经很冷了,怎样在“连长”——其实就是生产队长——查地之后美美地打个盹又不着风寒,是一门不小的学问。我当然学得了真传,而且在地里烤豆子的手艺也不赖——不过所有这套“磨洋工”的玩意到了自留地里就全然不见了。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人还是那个人,就是行为截然不同,劳作的结果也全然不同。
说起来,这是我修过的第一堂“经济制度与经济行为”课。不消说,当时还不可能得出清楚明确的结论。但是问题已经永远挥之不去:为什么同一个行为主体遵循完全不同的行为准则?也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知道自留地的来历——1960-1961年的大饥荒之后,才在一大二公的体系里划出了一小片自留地(有的地方干脆叫保命田)。今天说说也许无妨了:那年月例行公事的“忆苦思甜”,一位老农声泪俱下忆到的历史上最苦的日子,竟然就在1961年。这是什么样的诅咒?
要等到1978年以后,事情才有了一个答案。说简单也好简单,就是放手让种地的农民在大田体制和自留地体制之间作一个自由选择!说来也怪,让种地农民选出来的包产到户体制,不消几年就把原来的农产品高度短缺状态,变成了时不时农产品的“卖难”!陈云、邓小平无非就是坚持实事求是,坚决改革人民公社制度,用政策、舆论和后来通过的法律,承认并保护了中国农民选择的自由。

机缘巧合,从乡下考入北京的大学以后——那是我辈的一次自由选择——有机会在杜润生先生门下习过几年艺。我所知道的早期农村改革历史,就是不断冲破思想、体制和既得利益的笆篱,不断增加农民自由选择的历史。包产到户如此,取消种植计划、改革统购统销如此,允许农民办乡镇企业、进城镇务工经商亦如此。这样一路下来,即便愚钝如我,第一次读弗里德曼也不觉得有任何难明之处。惟一的问题是,他怎么可以把经济学道理说得如此清晰、准确和斩钉截铁的?
是的,必须是普遍的自由,而不是少数特权或既得利益集团的自由,才铺垫了经济增长的可靠根基。因为是普遍的自由,所以这“自由”就以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为边界。这样的自由,要限制政府权力的范围并对政府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但绝不主张“无政府”——因为离开了必要的政府强制和保障,自由一定荡然无存。我国农村体制变化的经验,从不堪回首到痛定思痛,再到从实际出发把土地变得充满希望,验证了弗里德曼简洁而深刻的经济思想。
后来在美国“洋插队”,结识到一位好朋友郭誉森。他当年从台湾到芝大留学,上过弗里德曼亲授的价格理论课,是货真价实的“芝加哥小子”。1989年我到美国后,经Gale Jonhson教授推荐在芝大经济系访问过9个月。认识后的第一次交谈(记得不在芝加哥),郭兄说你们在大陆写的东西,我差不多都读过了;有一点疑问,外边说大陆那时候封闭,但从你们报告的字里行间看,好像受过弗里德曼的训练,怎么可能呢?——回想起来,这是当时让我这个如假包换的“老土”最开心的一个问题。
1990年在旧金山,我才有机会第一次见到弗里德曼。刚刚开始学英文,不可能听得懂弗老的讲演,由誉森轻声为我一句一句翻译。那时全世界关心中国的未来路向,只听弗里德曼肯定非常地说,中国还要走改革开放之路。在场中外听众疑问重重,但弗老面不改色,解释说,他的根据就是原来计划体制的路线再也搞不下去,尝到经济自由甜头的人民决不会同意减少自由。
几天前听到弗老去世消息的一瞬间,我最先想到的就是16年前听他讲过的那一席话。天下学经济的都知道,弗里德曼最坚持经济理论和学说的高下惟一要由包含于其中的推测(prediction)来检验。仅从这一点看,弗老对中国走向的推测就足可以使他微笑地长眠于地下了。更不需要说,20世纪下半叶全球范围不同国家的改革实践,早已经是“米尔顿法则”的最好检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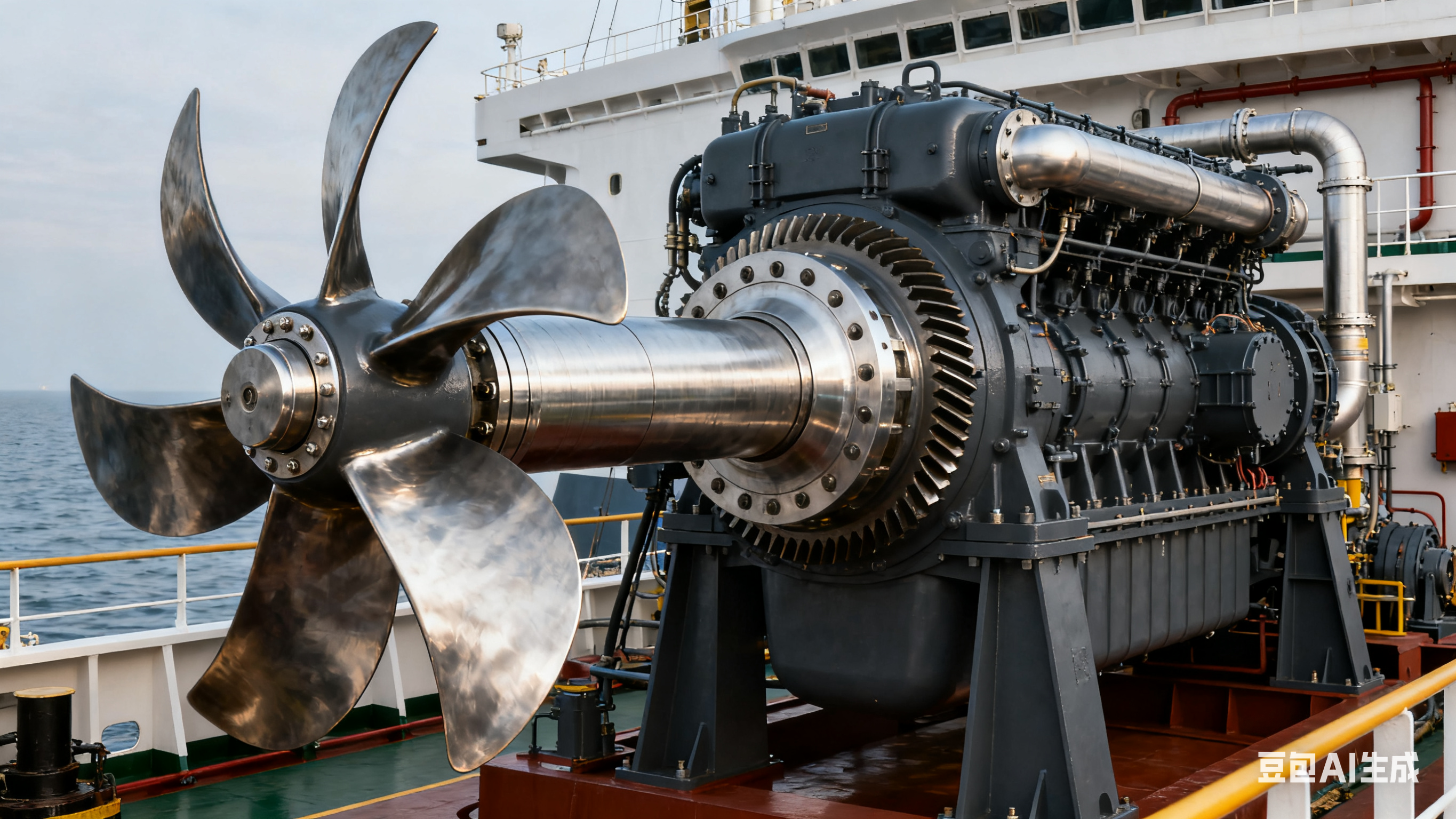


















请先 登录后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