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祖国的飘
飘。在大金融领域接近20年,现居欧洲。下面是她的口述。

在国内,我从小就跟环境格格不入。学校要求头发不能太长,要带发圈,我不喜欢。我想跳舞,但他们不让我参加舞蹈队。学校只讲为学校争光,要拼成绩,但我只想要快乐。我本来想进体操省队,但不让我进,说我骨头宽了,虽然我的技能很好。
在应试教育里,在集体大于个体的文化里,好像每个学生都是产品,我是亿万分之一,个性没被在乎过。虽然现在90、00后能更多的追求爱好,但我那个年代很难,这跟经济发达程度相关。
我第一次出国是去澳洲上大学,第一堂课,教授说,这里有两种观点,你们选一种来支持,也可以有自己的第三种观点,并没有对错之分,只要自圆其说就行。
居然没标准答案,这是第一个文化震撼。可这个从天上掉下来的自由,我当时却不知道怎么办,手足无措,还害怕挂科。
后来慢慢融入本地,开始一种漂移生活。澳洲、新加坡、美国、英国、现在意大利。今天如果再回国,我肯定水土不服。
国内阅兵,都是一米八的大个子,整齐划一,澳洲阅兵,人都是高矮不齐。在澳洲,有个同学代表国家参加奥运会,但她比我胖,比我矮。在国内基本不可能。
在澳洲,有次我大出血,被大家送去医院,我感觉到我被看见,被在乎。在英国,我拖着箱子在地铁里找电梯,有六个人过来问,要帮我提箱子。
在国内,我带娃出去,好像有原罪。娃一闹,人会指责你。但在米兰,路人会对你一笑,意思是我也理解你的烦恼。他们会跟我的娃玩游戏,安慰他不要哭。
中国是我的生母,西方是我的养母。生母把我养大,让我有离开她的力量。养母也给了我足够的善意。
飘,就是适应不同价值观。小时候在国内接触到的主流价值观是,要功成名就,一切向钱看,这不是我想要的。我追求新鲜感,换地方,换行业。
毕业三个月我就离开澳洲,因为地方太小,2000万人。我的同学说,如果留在澳洲,去家投行,每天加班到凌晨,拿10万澳币,可本地的矿工可以拿20万澳币。
有一段我回了国,做并购,一周工作100个小时,一年飞10万公里。忽然有天想休息一下,就去英国上学。
在伦敦这个学校,只有11%是英国人,其他都是全球来的。英国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有强烈的美国文化,大学里有60%是美国学生。伦敦是大熔炉,不同的人种、价值观、爱好,杂在一起。
学还没上完,我就给老板说,我不想回去了,我把学费还给你。然后就留在伦敦。后来我先生外派,本来可以去阿根廷、泰国,但选了米兰,因为我对欧洲历史感兴趣,想在这里待四五年。
我身上有主流的外衣,但过着不主流的生活方式。我是现代游牧民族,对哪个地方都没有百分百的认同感。生活方式可以随着改变,这源自我的幸运,当然还有努力。拿到牛津剑桥这种文凭,是硬通货。可以拿到global pay,去全球都是一样的工资。
工作强度,中国大于美国,美国大于英国和澳洲,它们大于德国、法国、意大利。德法意的生活方式非常松弛,就算中国人,在那里到了三点半也要午休,在国内不可想象。
生孩子前,我的生活方式还是单一,只在名校校友这个圈子。英国新生儿里,叫穆罕默德的已经排第一,但我身边有50个国籍的朋友,一个穆罕默德都没有。
但生娃后进了妈妈群,才发现什么样的生活都有。伦敦能满足很多人的想象,这里全球百亿富豪最多,也有历史,有自然,可以满足各种小爱好。只有天气不好。
伦敦有很卷的人,可能占5%,基本在金融、法律这种服务业,每年给英国带来几百亿出口盈余。这些人一年挣几百万英镑,一周工作100个小时。但也有不卷的,你生两个娃,政府帮你养,还管你吃住。
我慢慢脱离了中西对立的思维,西方其实是个泛化的概念,英法也打了很多年仗,民族性大不一样。英国和美国是相同民族和语言,但也有差别。好像广东跟北京也不一样。
我现在像是摘不同的果子,喜欢的某种文化元素,就融进自己生活。不同民族像钻石一样,有不同的切割面,不同的民族性。
中日韩是集体责任大于个人主义,不容忍outlier。英美是个人英雄主义,好像肯尼迪说的,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欧洲跟道家异曲同工,讲究天人合一,和谐。非洲和南美是快乐主义,享受高于一切,今朝有酒今朝醉。
英国人对逆境很坚韧,可能是被糟糕的天气逼的。尤其冬天的雨,非常冷,非常凄凉,那时农作物也很少,有时只能吃土豆。
英国人对不抱怨的要求很高,认为抱怨是不考虑别人,是自私。英国人很隐忍,对食物不满意,他们心里说,像屎一样难吃,但面子上也说好吃。
英国人冷漠,不扎堆。意大利人不同,跟中国人有点像。扎堆,说话声音大,喜欢交朋友,熟人社会。可能因为在南欧,被阳光晒出来的热情。
法国是时装,瑞士是制表,他们都有工匠精神,做热爱的东西。
瑞士,约定好的时间,要提前10分钟到才不算迟到。德国,必须一分不差。英国,迟到5分钟以内都可以,但要道歉。
但意大利,迟到半小时都正常。曾经中国有个行长去意大利开会,对方部长迟到半小时才来。
有个孩子去意大利读书,回了德国老家,中午12点吃饭的时候一过,老爸冲进他房间说,你下次迟到一分钟,就滚出去。
在英国,我们感觉不到贵族的存在,其实英国皇室是吉祥物,是对外市场推广的手段,可以挣观光收入。但在日常,他们没有影响。
到了米兰,才发现贵族真实存在。有个朋友是米兰出生,父母是跨国公司高管,有几十套房子,好像包租婆,但也进不了的贵族的圈子。在米兰贵族眼里,他们也是乡下人。好像在法国,巴黎人认为巴黎以外都是乡下人。
是不是贵族,看名字就知道,好像一个标签。贵族就觉得我是中心,相互抱团,封闭起来。欧洲大陆讲血脉,不是只认钱多。
贵族看重血脉,不跟平民通婚。但又害怕近亲繁殖,所以欧洲各国贵族相互通婚,意大利的去找瑞典的。这是老系统,要维持自己的归属感。
贵族有爵位,有封地,所以很多靠收租。但现在土地不大值钱,他们也会去银行打工,也会跟美国的有钱人通婚,这是一种变现。
逐渐的,我开始更客观的看国内。经济奇迹很难复制,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我妈妈做生意赚钱,也不能送我出去读书。权力集中,效率很高。好像车子开的快,漏点油也没关系,但波峰波谷大。
一对比,英国换首相比换衣服还快,非常短视,英国人搞怪,把唐宁街10号画成AIRBNB,嘲笑这是短租房。所以这个系统很慢,内耗很多。苏格兰就一直闹独立。但硬币的另一面,这也是纠偏机制,搞砸就下岗。
可日不落帝国一直在往下走,也没人站出来,彻底扭转这个趋势。所以老百姓认为,英国这个体制,符合现世安稳。它不一定比中国好,但没有波峰波谷,对中产小家庭适合。
一个国家有它的发展逻辑,这改变不了,是命运。把一个事做大之后,就被无法改变的惯性。所以每个国家有自己的解题方式,英国的不适合中国,中国的不适合印度。
我也想让孩子学些中国文化。这是身份认同。我在外面跟人介绍自己,会说我是Chinese。中国的古诗词很好,并且双语对智力的开发有好处。但现在国内感觉太卷了,回去花钱很爽,挣钱太累。
有次我回国内,点外卖,本来一小时,结果20分钟就送到。但少了一盆菜,我就打电话,老板问,是退款还是重新送。我就惊了,在英国绝不可能有重送这个选项,人力太贵。
我就说,退款。老板又说,我们可以送。我还是要求退款。但我先生说,可能重送更好,他们害怕失去这10块钱。
我对国内有了更多理解,但同时,国内也要对其它国家有更多理解。世界是没标准答案的。
有人嘲笑印度阿三扶不上墙,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但印度的call center为西方服务,还有码农,都很强。在英国最好学校里最卷的人,印度第一,俄罗斯第二,华人妈妈只排第三。印度整体更像无为而治,很多很厉害的人都有个人奋斗史。
有个印度朋友,爷爷做珠宝品牌,她老公很穷,靠刷盘子在伦敦上学,靠叔叔救济住在地下室。现在是私募基金合伙人,年薪几百万英镑。
有个朋友是富二代,她老公来自一个欧洲小国,名字都很少听到那种,就是学霸,自力更生,做了个科技企业,几千万卖给uber。
所以英国也厉害,在全世界搜刮聪明人和钱。前一段英国没收一个中国人2000万英镑,那是个贪官,我觉得不公平,那是中国老百姓的钱,凭什么被英国没收。但又不得不服气,他们真能逮到贪官,也能抽丝剥茧找到藏起来的钱,真敢没收。
日本有个寿司大神到伦敦来开小馆子。我说,伦敦的寿司馆不是很多吗。有日本朋友就说,这个人很厉害,他放弃日本的一切,就为了小孩读书,他们认为伦敦有最好的私立教育。
伦敦的私立教育,市场推广做的好,这是它的出口赚外汇的项目,招一个国际生的学费是本地人三倍。它号称全面教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而且一路上去进牛津剑桥容易,有确定性。好像你要读人大附中,最好读它的初中。系统内的确定性。
一旦拿了牛津剑桥的学位,基本上衣食无忧,好像中国的清北。在这里只有清北校友会,我身边的人都是出自那十几家全球名校。像个bubble,所有人都是相同背景。
现在有很多全球化人才。有个朋友是克什米尔人,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起冲突那个地方,父亲是外交官,他去了无数个地方,他说他属于nowhere。
我起初觉得他无病呻吟,但后来渐渐理解了这种心理问题,就是飘着的状态。这是我的选择,有个回不去的故乡。我选择兼收并蓄,不受任何系统的束缚。
我现在拿什么国家的护照,只因为这个护照好用而已,我不认为我是意大利人,或者欧洲人。我儿子说他是中国人,我也不希望他成为意大利人,文化的苗还在中国。
很多中国人出来,但赚钱还是离不开中国。我现在赚钱跟中国基本没关系,有松一口气的感觉。我不依靠任何国家,也不打算建设英国或者意大利。好像野种子,哪里都能发芽。
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我是逐生活方式而居。自从工党在英国上台,我觉得经济好不了,就离开。等这一波过了再回去。
我在南欧享受阳光沙滩,还有水果实在太好。英国除了草莓苹果,其它都种不出来。英国,60%是深加工食品,意大利只有10%,所以英国人亚健康多。
我在大理住过,馆子里科技狠活很多,我只能自己做饭。在国内要吃同样的有机食材,花费比英国翻倍。
中国人不了解欧洲,全部精力都放在美国,反过来欧洲人也不了解中国,彼此有很多误解。今天欧洲人还觉得非洲是它的附属地。
我说英语,米兰人会觉得我是日韩人,他们潜意识觉得,会讲英语的都不是中国人。他们印象中的中国人,是浙江农村来的,在工厂里打黑工。
八九十年代开始,中国大量翻译西方的书籍,什么经典都能找到,但在西方基本上看不到中国的东西。在英国,除了好莱坞在电视台放,要看德语片、法语片都得自己找,更不说日韩和中国片。整个社会并不开放,所以他们觉得中国崛起是个谜。
如果中国和欧美彻底脱钩,甚至冲突。我觉得华人个体在欧美还是安全。相对来说,美国护照的保护力低于英国护照,因为美国曾经对日裔种族隔离。
德国人跟日本人也不一样。德国人为二战拼命道歉,但日本人不是。德国朋友说,德国人不会再发动世界大战,他们受的教育就是那样。
问:你的太极球是什么。就是打通阴阳,不让对方互害,而是相生。
飘:我是达尔文主义者。我认为人生没有长期意义。活着的此刻,每一秒的体验就是意义。这一秒过去了,这个意义就消散了。
就如这一秒,我站在罗马的阳光下,给你拼命打字,直抒胸臆,这是我此刻想做的事,就是我生命体验的意义。
我能做的最长期的事,就是投资。以前是为了我愿意活着的每一秒提供弹药,现在是为了我儿子活着的每一秒提供弹药。我死了,他死了,意义就消散了。
如果非要说我追求什么,就是“从心所欲不作恶”。对我来说,我的个人自由高于一切。但我有我个人定义的道德约束,就是主观意愿上不伤害他人,不犯法。就这个,其它任何社会成规都不能约束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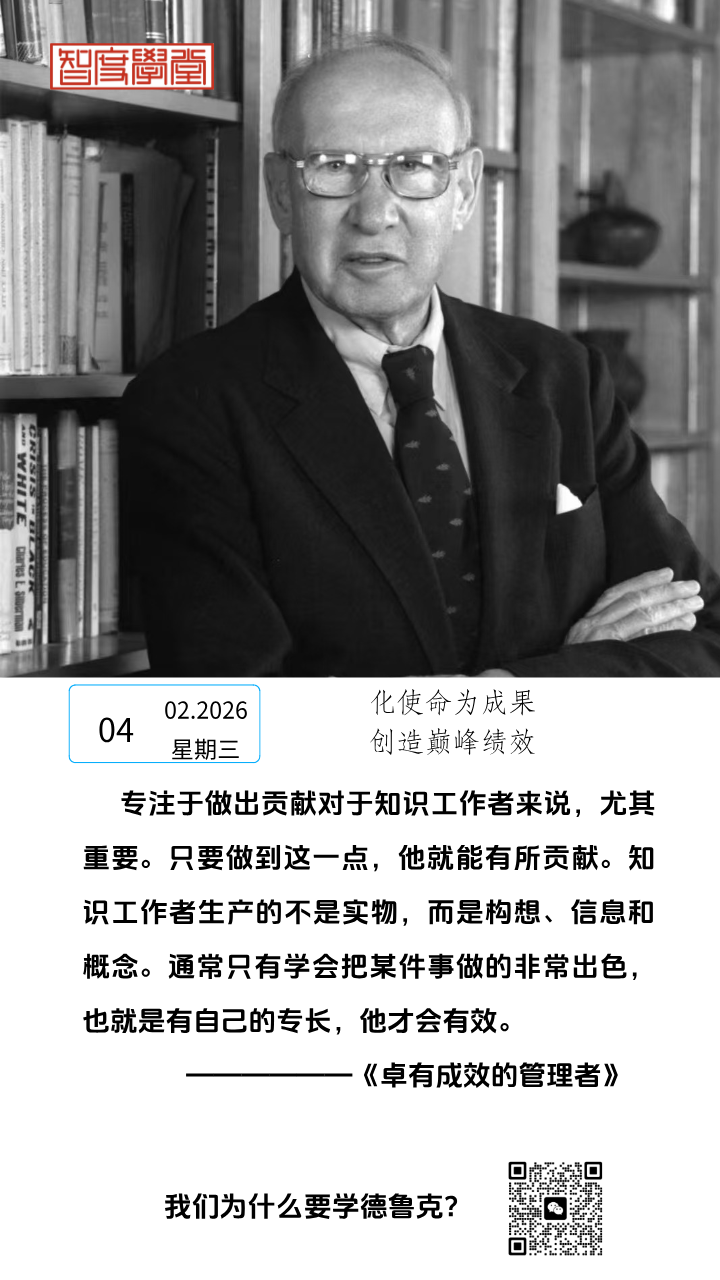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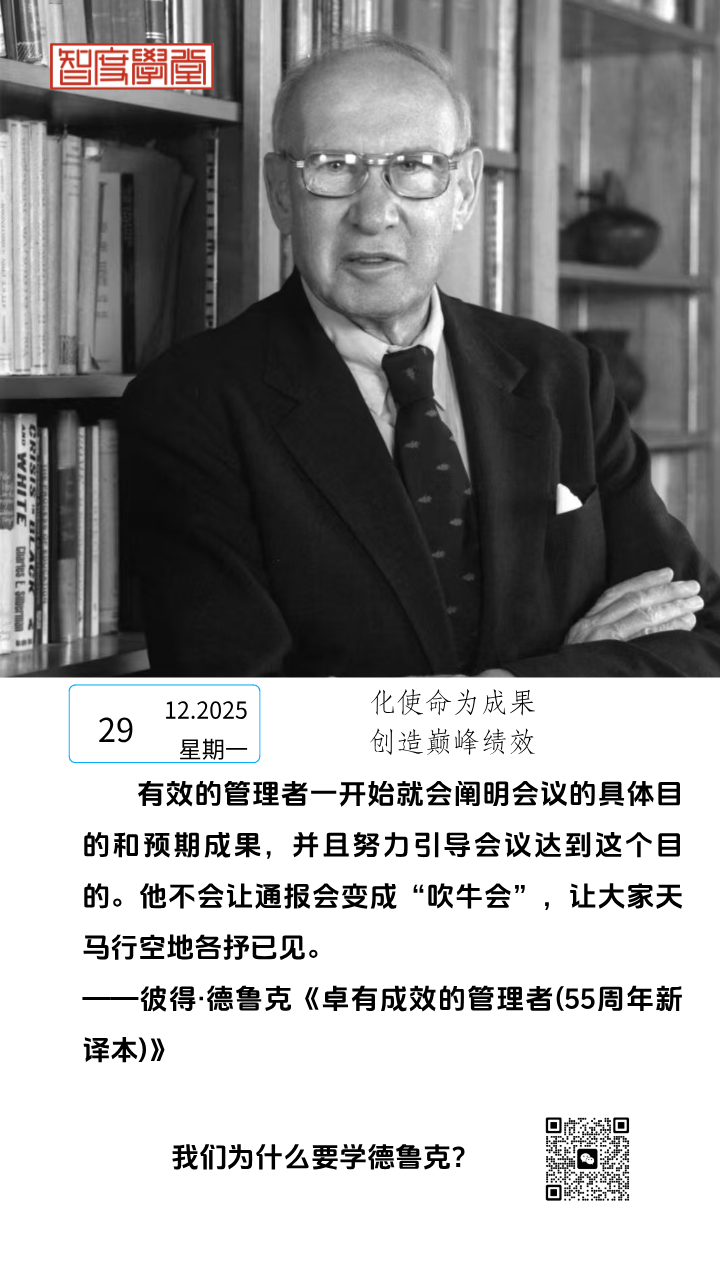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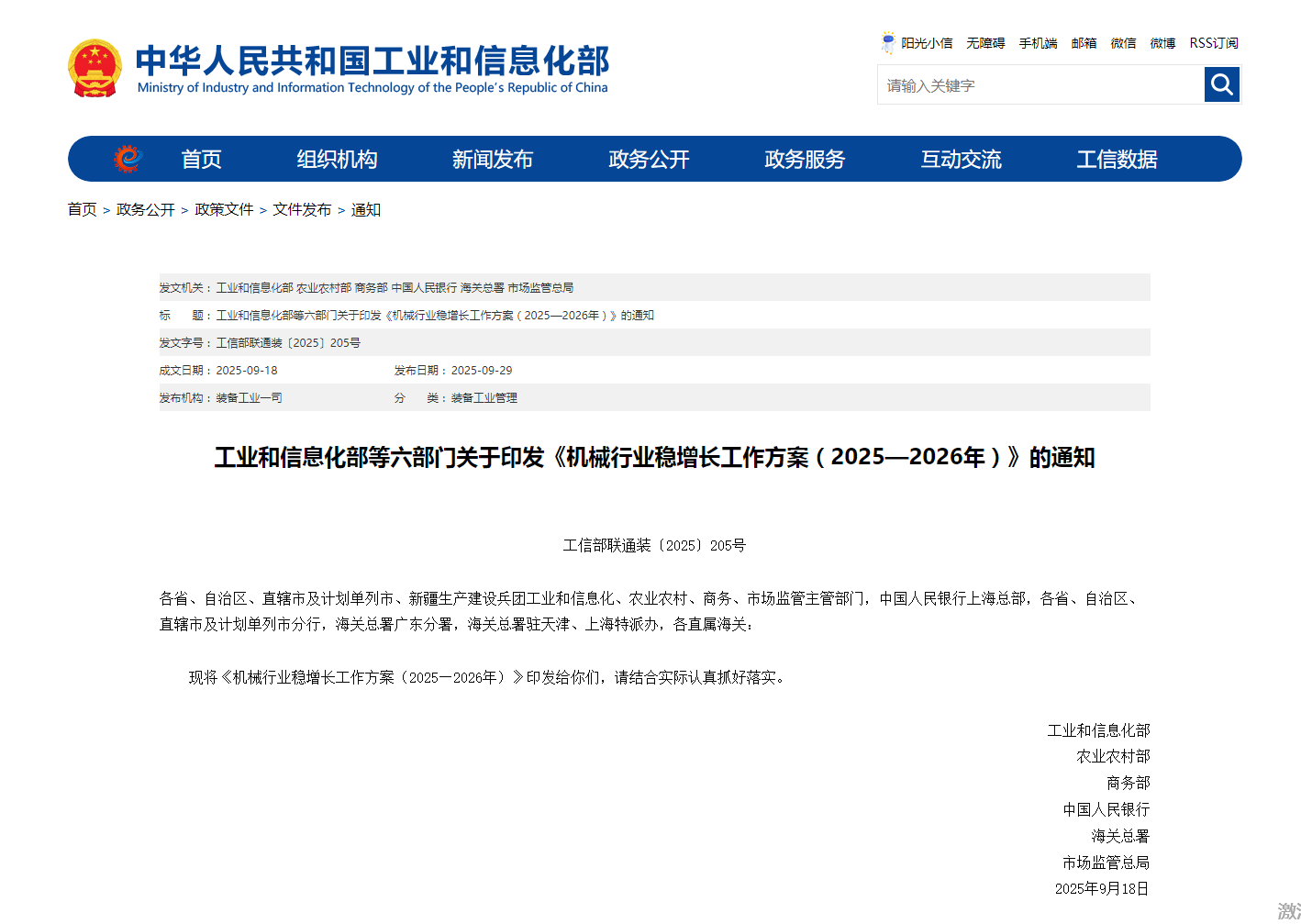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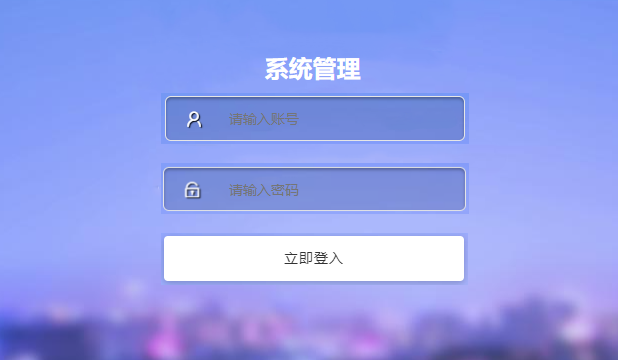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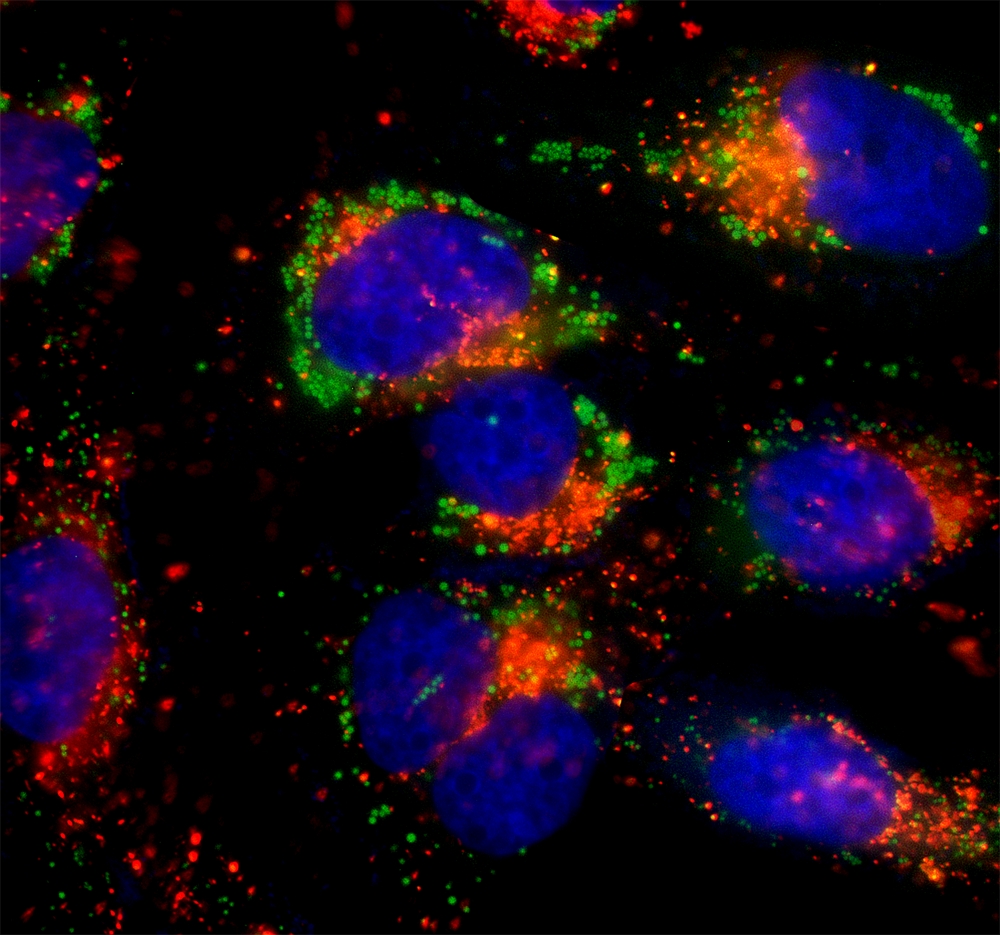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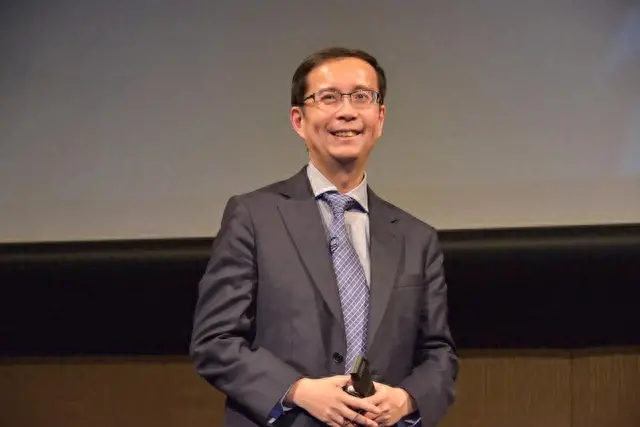











请先 登录后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