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创业大街:“创业是一种病,惟有甘于平庸可以治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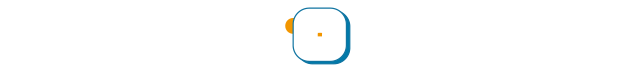
正午时分,北京马路上的地面气温竟高达39度,天高云淡,整条创业大街像是被阳光洗过了一遍,一尘不染而空寂无人,如同这个时代的某一个侧面。
上次见到苏菂是2019年,我拍摄《地标七十年》,先是去了车库咖啡,然后拐到对面的中关村创业博物馆,在几台老苹果电脑前,跟他有过一次对话。这次去,车库咖啡还在,博物馆早在三年前就关闭了。上次去的时候,创业黑马在那里有一个四层楼的空间,我跟文文曾很开心的聊了很久的天,现在,创业黑马也搬走了。
创业大街很短,只有200米。它原本是海淀图书馆与对面一栋建筑物之间的一个露天过道,2011年,32岁的蓝汛前投资总监苏菂在这里开出了全北京的第一个创业者共享空间---车库咖啡,听名字就知道,他在致敬硅谷。
“那时,整条街上都是卖二手书、盗版碟和乐器的小店,车库咖啡开在二楼,底层是李先生面馆,面积有800平,我装修只化了14万元。没想到,几个月后竟人满为患。”
在车库咖啡的墙上,迄今还挂着八九块牌子,小马哥指着其中一块告诉我,就在2011年底,中关村管委会授牌这里是“集中办公区”,在此之前,北京市申请营业执照都要有独立的办公地址,授牌之后,只要在车库咖啡租一张桌子,就能办公司了,这是全中国的第一例。

2015年5月,时任总理到创业大街考察调研,谈笑行走,还喝了一杯“创业者咖啡”。此后,这里便成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标杆之地。极盛时,短短的200米大街上,涌进了二十多家创业孵化机构,日喧夜嚣,热闹非凡。
夏至那天我去的时候,三分之二的机构已经撤离,留守下来的,也全数寂守空巢。忆及往昔,恍若隔世,其实细算,不过数年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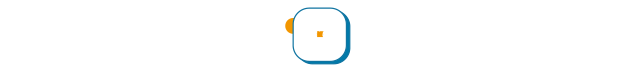
我这次重返创业大街,并不是去“凭吊”,而是苏菂约我,谈一个新的众创空间项目。
我问苏菂,创业大街的衰落,原因是什么?
他的回答颇有点出乎我的意料。在他看来,不是没有了创业者,也不是没有了创业的机会,而是思想碰撞氛围的稀薄,以及创业精气神的流失。他看过我写的《回来吧,“疯子”们》的专栏,很有共鸣,“现在要把疯子们都叫醒来,重拾丢掉的精神内涵。”
夏至那天,有两个细节还是令我颇为感慨。
我跟他行走在创业大街上,迎面而来的第一个人,居然是车库咖啡早年的一位职员。他跟苏菂也有十年没见了,就这样偶遇撞见。这些年,他一直在南方创业,这次到北京办事,特地来大街上逛一下,“其实也没事,也没约人,就是,那份念想。”
在车库咖啡馆,偌大的空间只有零星两三桌的人,服务员杨姐在这里干了十来年,好像有几个月没有领到工资了。不过,在一堵“招聘墙”上,仍然贴满了各色纸条,有一些显然是新挂上去的,有元宇宙、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语言技术的等等,仿佛灰烬未熄,仍有火花闪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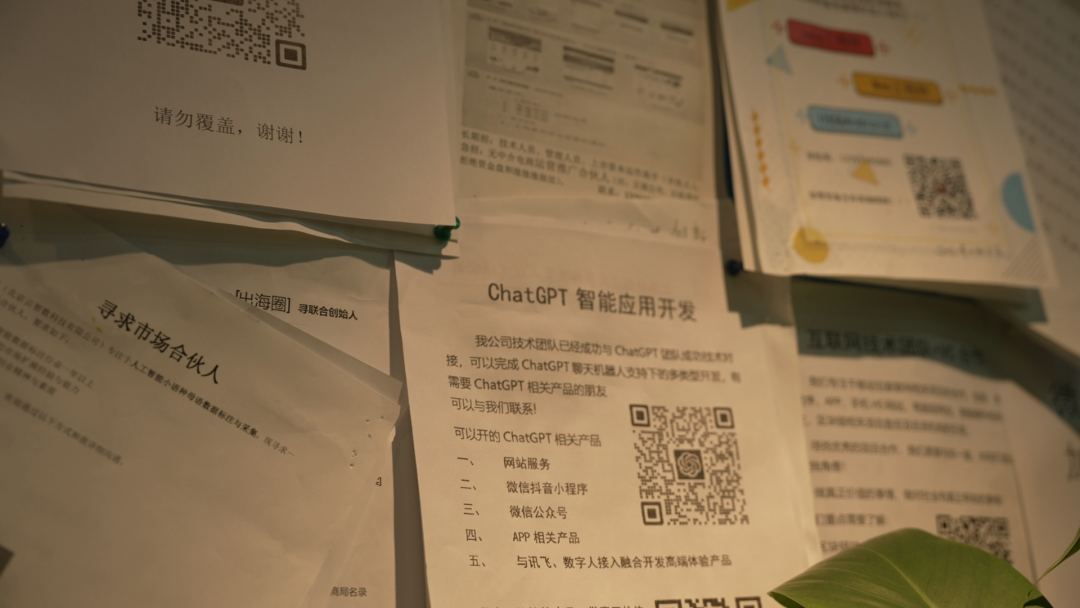
他动这个念头,是在今年的3月中旬。“我跟西城区几个管科技的官员聊起,想要重启一个创业者空间,他们很来劲的样子,我的劲头也被吊起来了。”
在过去的三个月里,苏菂找到西城区马甸的一处小茶馆,开始坐堂布道。“我已经见了1000多个人,讲了300多遍,特别兴奋,单是瓜子就吃掉了1.3万元。”
尽管创办车库咖啡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情了,这位年过不惑的北京人似乎还是创业梦的重度患者。在一遍又一遍的讲述中,他的新项目日渐的清晰了起来,围观助拳的人越来越多,甚至把远在杭州的我也裹挟了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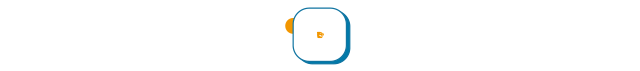
创业是一种病,惟有甘于平庸可以治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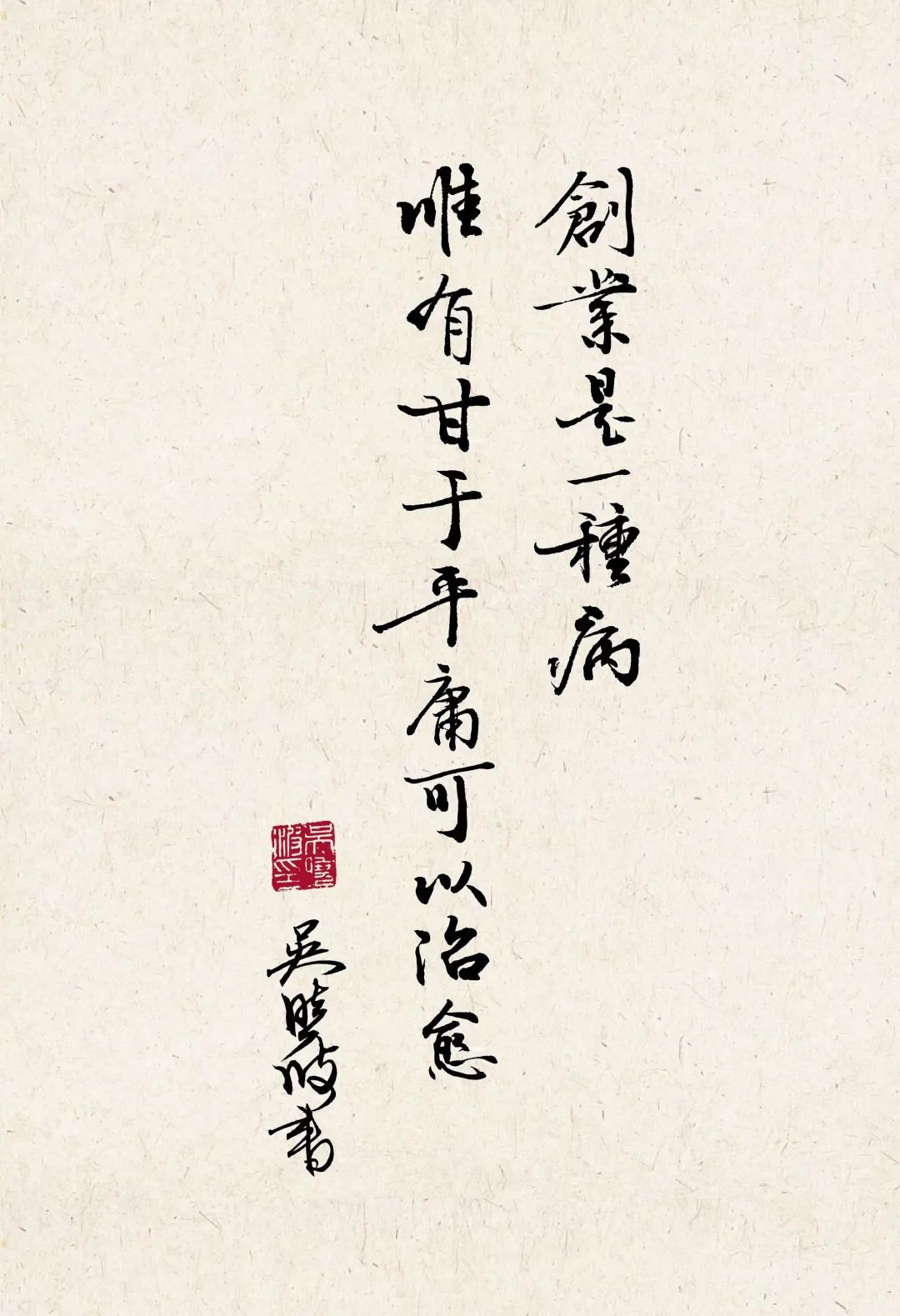
而十年前最近的这一轮创业,第一次呈现出全民狂欢的特征,可谓是地不分南北,人不论尊卑,俱以创业为荣事。创业大街的繁荣,正是其中最具象征性的一个景象。
在我看来,也是从此之后,中国出现了一个“创业者阶层”。
如同《史记》里的游侠、中世纪的欧洲骑士、日本武士,以及现代美国的牛仔,创业者在当代中国,构成为一种独立的职业以及精神气质。它发生在所有的行业,同时以破坏者的姿态追求过程中的“极致体验”。
作为一支前所未见的社会力量,中国的创业者群体形成了独特的阶层共情和主体意识,他们突破了传统社会的理性主义思维,用非常规的方式思考商业的价值和找到“自我”。
与1960年代末的欧美青年相比,中国的这一代创业者同样是属于“嚎叫”(艾伦·金斯堡)和“在路上”(凯鲁亚克)的一代,所不同的是,他们将所有的热情、愤怒和颓废都灌注于商业,而非其他的人文和社会关怀。在某种意义上,创业是那种能够产生幻觉的生活方式,它特别适合发生在大中城市。
在今天,所有关于创业的讨论,要么沉沦为“躺平”,要么归宿于陈词滥调,但是,这股社会力量其实并没有死亡,或者还远远没有到终结的时刻。我的兄长牛文文尽管搬离了大街,而创业黑马仍是中国最积极的创业推动者,现在,苏菂们的蠢蠢欲动,更是最新发生的一例。

苏菂还没有为他的新项目想好名字,用他的话说,“还没有被雷电击中”。不过,空间的地方已经找到了,它在马甸那个小茶馆旁边的一栋大楼底层,有2000多平方米,现在是一个空寂的设计共创中心。

空荡的设计共创中心
在他滔滔不绝的讲述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个词是“开源”。在他的构想中,这里将有开源的技术,开源的硬件,开源的资本,更重要的,当然是开源的思想和不甘平庸的人们。
从创业大街出发,我跟他赶到那个暂时驻扎的小茶馆,一推门,便见到了十多个正在那里热烈讨论的苏菂的朋友们。我见到了多年不见的老友、中国第一代网游创业者鲍岳桥,其他的人大多都是当年车库咖啡的参与者,有两位竟是从佛山和贵阳赶来的。

这是一群被困在时间舱里的人们,“疯子”的基因从创业的第一天起就被种下,岁月磨去棱角,但压抑的热血却始终暗流未绝。在那间简陋的茶室里,我看得见他们眼中的光,既野性又温暖,宛如失散的兽类重逢,嗅到彼此熟悉的气味。
苏菂让我猜:“那两个800人的群里,是哪些人?”
我说,“应该90后是少数吧,不会超过三成。”
他大笑着说,“90后不到一成!这就是车库咖啡的2.0,未来的新空间里,最多的当然会是95后和00后,但是,还有很多踩过坑、死去活来几百次的老兵跟他们在一起,前去冒死创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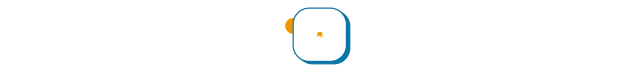
此刻,我坐在杭州的书房,开始写作这篇专栏。
我仿佛又回到了创业大街。
我看见,有人摸黑出发。
创业者被嘲笑为“失败者联盟”。在2020年前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每天有一万家创业公司,他们中的97%会失败于此后的十八个月里。人们看到的所有成功的创业故事,都是“幸存者偏差”,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结果。
但是,少数人的成功,推动了中国商业的风起云涌,而绝大多数的年轻失败者,在无比痛苦的历练中完成了自己的精神磨炼,并拥有了一份无可替代的生命记忆。
在很多创业者的一生中,最难忘的人和事,是他们的初恋情人和创业经历。如同那个我和苏菂在创业大街偶遇的前职员,重走一趟,只为念想。
在今天,虽然经济不太景气,然而,如果你回到产业基本面,仍然能发现无数的新机遇、新需求和新的可能性。认真的想一下,对于那些有梦想的年轻人,唯一可以自我救赎的,很可能还是九死一生的创业。
所以,我愿意写一写苏菂,愿意为他的新项目绵尽薄力,愿意跟他一起,回到“创业大街”,为新一批的“疯子”们的重新出发,呼喊一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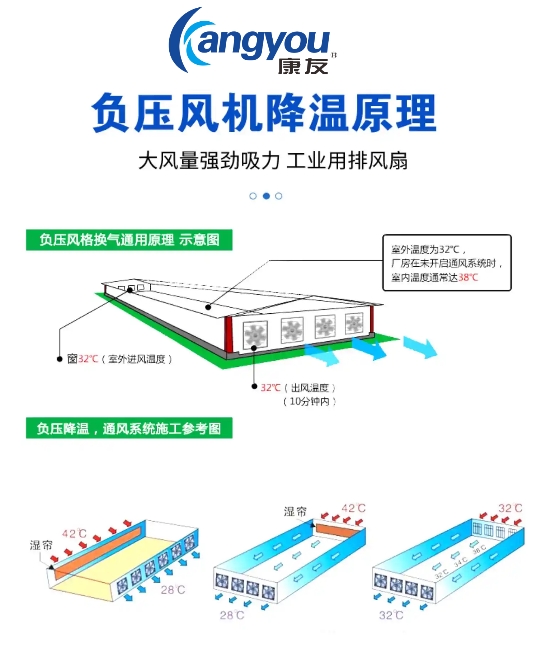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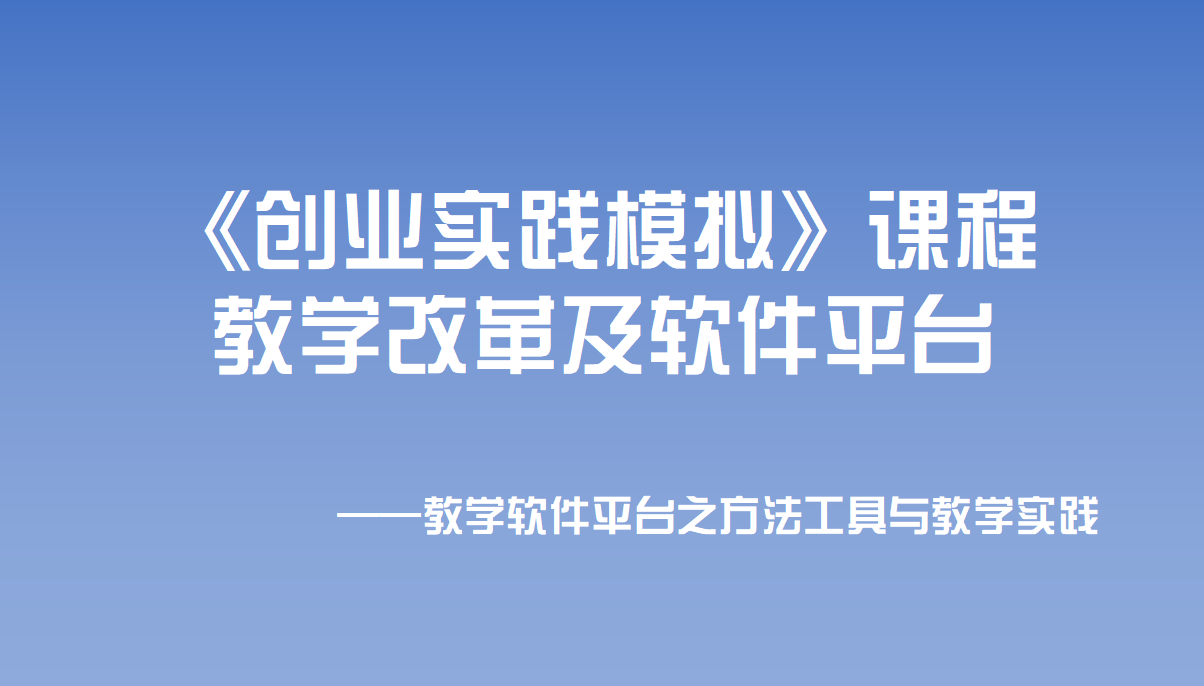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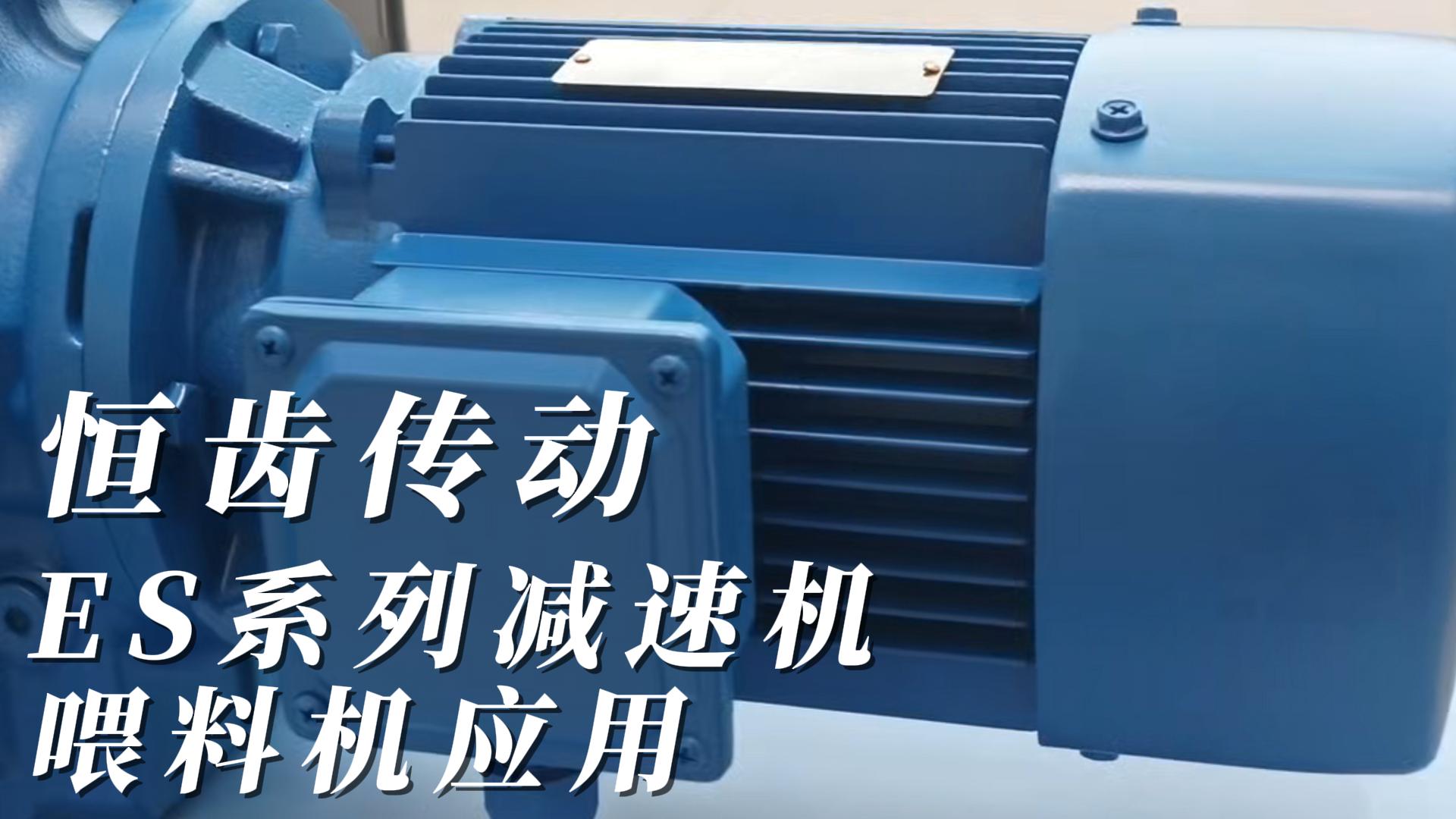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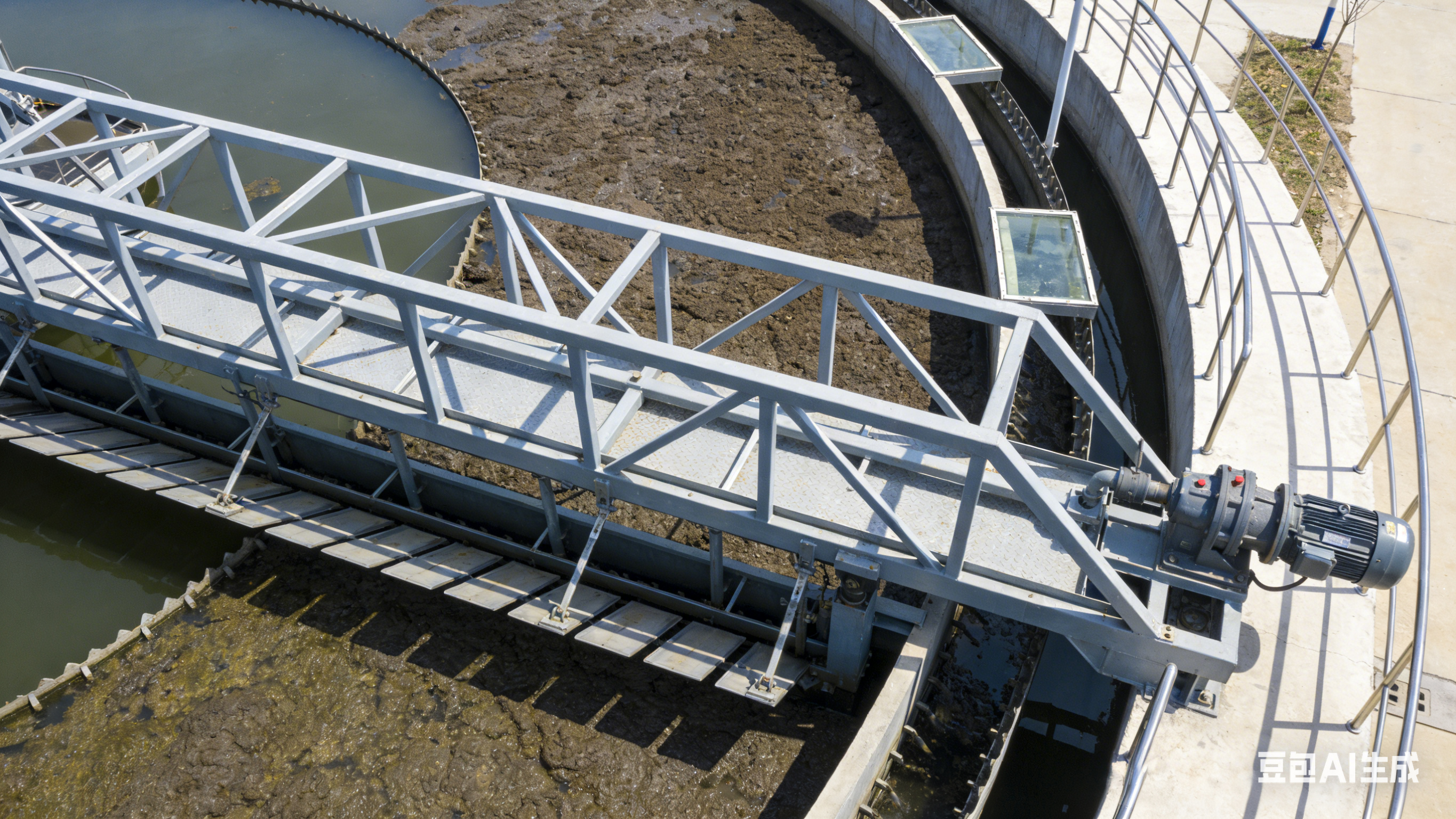















请先 登录后发表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