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想要金饭碗与铁牢笼,这是社会悲哀!
盛夏,北京天热,我近来是不大出门的,但偶尔踱步到街上,或是在夜深时翻看些网络上的消息,便总能感到一种沉闷的空气,黑压压地罩下来,叫人喘不过气。这种沉闷,不是来自炮火,也不是来自饥荒,而是来自一种集体的、安详的奔赴——奔向同一座“围城”。
你看,那些书店里最显眼的位置,堆着的不再是思想的巨著,而是一摞摞的“上岸宝典”、“通关秘籍”。翻开看时,里面的字,密密麻麻,像无数只蚂蚁,教人如何揣摩,如何应对,如何在一个固定的方框里,画出最标准、最讨喜的圆。再看那些年轻人,本该是眼里有火、心里有梦的年纪,却一个个面色凝重,锁着眉头,仿佛提前几十年就背上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唯一的指望,便是挤进那扇窄门,捧上那个据说风雨不侵的“金饭碗”。
从垂髫小儿的志愿填报,到而立之年的“再搏一把”,浩浩荡荡,千军万马,都朝着一个方向。这景象,初看是壮观,再看是滑稽,细想之下,只觉得彻骨的悲凉。
一个偌大的国家,无数的聪明才智,竟不约而同地将“安稳”二字,奉作了人生的最高圭臬。仿佛创造、开拓、冒险,都成了不合时宜的疯话;而那份稳定的、按部就班的、一眼能望到退休的生涯,反倒成了无上的荣耀。
这究竟是怎么了?
有人说,这是现实所迫。我晓得。只是,当所有人都将躲避风浪作为唯一航向时,这片大海,也就彻底失掉了生机,成了一潭望不到边的死水。整个社会,仿佛一个巨大的漩一涡,我们称之为“内卷”。它不创造新的价值,只是在有限的存量里,耗尽心力地争抢、撕咬、彼此消磨。
人人都想成为分蛋糕的人,却没人再去想如何把蛋糕做得更大。于是,最好的资源,无论是教育还是医疗,都水银泻地一般,流向了那个体系。这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和分配逻辑,是计划时代幽魂不散的遗产。
权力,是会带来傲慢的。在一个封闭的、等级森严的体系内,人与人之间,是一种微妙而长期博弈。大家在无形的规则里,消磨了锐气,学会了世故,把棱角磨成圆滑的卵石。这样的土壤,是长不出参天大树的,更容不下一个敢在铁屋的墙上凿个窗户的人。
那些不安分的魂灵,那些真正想创造点什么的人,他们的结局,我似乎也曾见过。要么,是他的创造力被视为一种威胁,最终被这巨大的惯性所碾压、所吞噬,落得个“寻衅滋事”的下场;要么,是他自己先被这酱缸染得失了本色,最终成为他曾经最不屑的那种人。于是,创新死了,活力没了,只剩下一片死气沉沉的“和谐”。
然而,那看似坚不可摧的“金饭碗”,那被无数人信奉的“保护伞”,就真的那么牢不可破吗?
历史,是喜欢开玩笑的。它常常于无声处,让那些看似永恒的偶像,轰然倒塌。我时常想,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当人们赖以为生的信条,在一夜之间化为齑粉时,那一张张惊愕的、茫然的脸,将会是怎样的一番光景?那份震惊,恐怕比任何灾难都来得更加猛烈。
写到这里,窗外的夜更深了。我并不想兜售廉价的绝望,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我只是想说,尤其是在这艰难的日子里,我们或许更应该抬起头,看看那扇窄门之外的广阔天地。
希望,在哪里?
它不在那人头攒动的考场里,不在那堆积如山的手册中。它或许,就在某个不被看好的角落,在某个甘于寂寞、埋头苦干的身影里;在那个敢于质疑、敢于走上少有人走的路的年轻人心中。它是一种韧性,像石板下奋力生长的小草,于沉默中积蓄力量,于黑暗中寻找微光。
人们说:“你不要太理想主义。” 我说:“你不要太快忘记梦想。”
一个国家的希望,不是人人都想当公务员,而是还有人愿意去当科学家、诗人、创业者、乡村医生、小镇老师——那些看起来“没保障”的角色,其实才是一个社会真正的底色与生命力。
我们不必都成为英雄,但至少,可以努力不让自己成为那梦游队伍中的一员。守住自己的一点真,一点热,一点不甘平庸的火种。因为,当铁屋里的大多数人都在沉睡时,那几个辗转反侧、保持清醒的人,就是这片土地最后的、也是全部的希望。
——不从众,就是一种微小而真实的勇敢。
愿我们,都能在寒夜里,呵护好自己胸中那一点点,珍贵的余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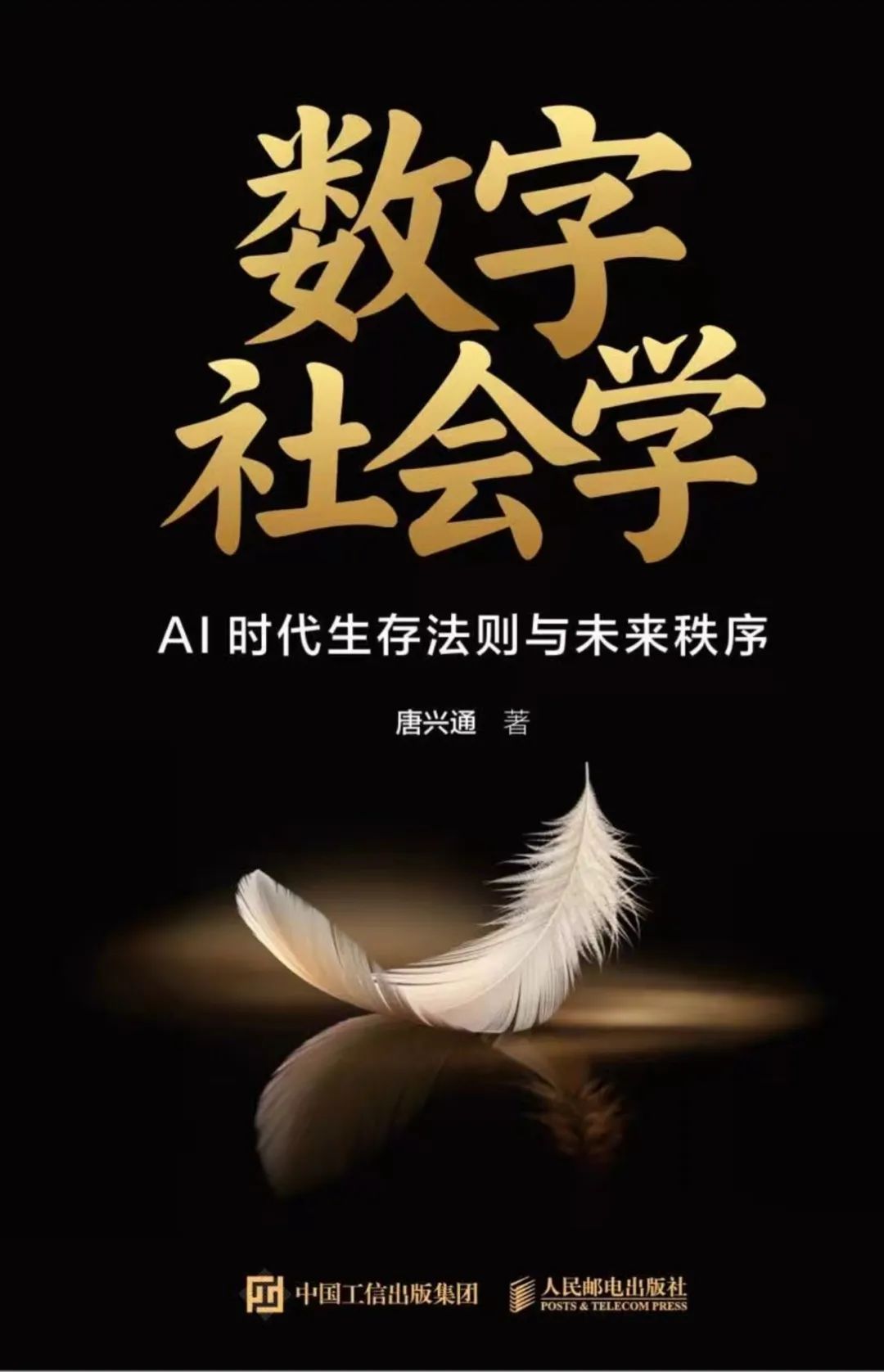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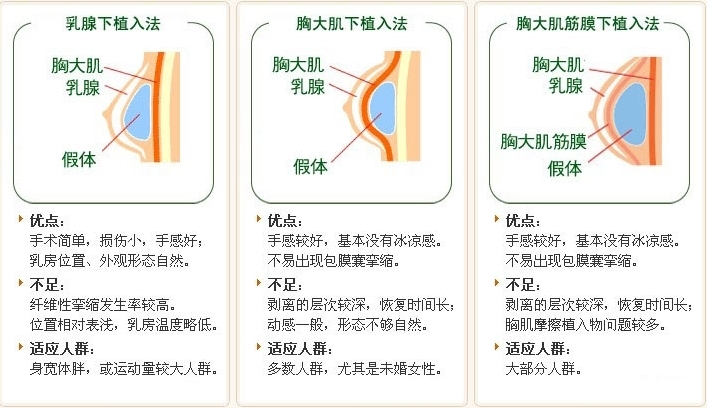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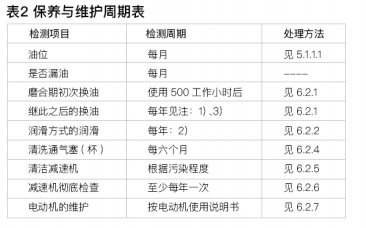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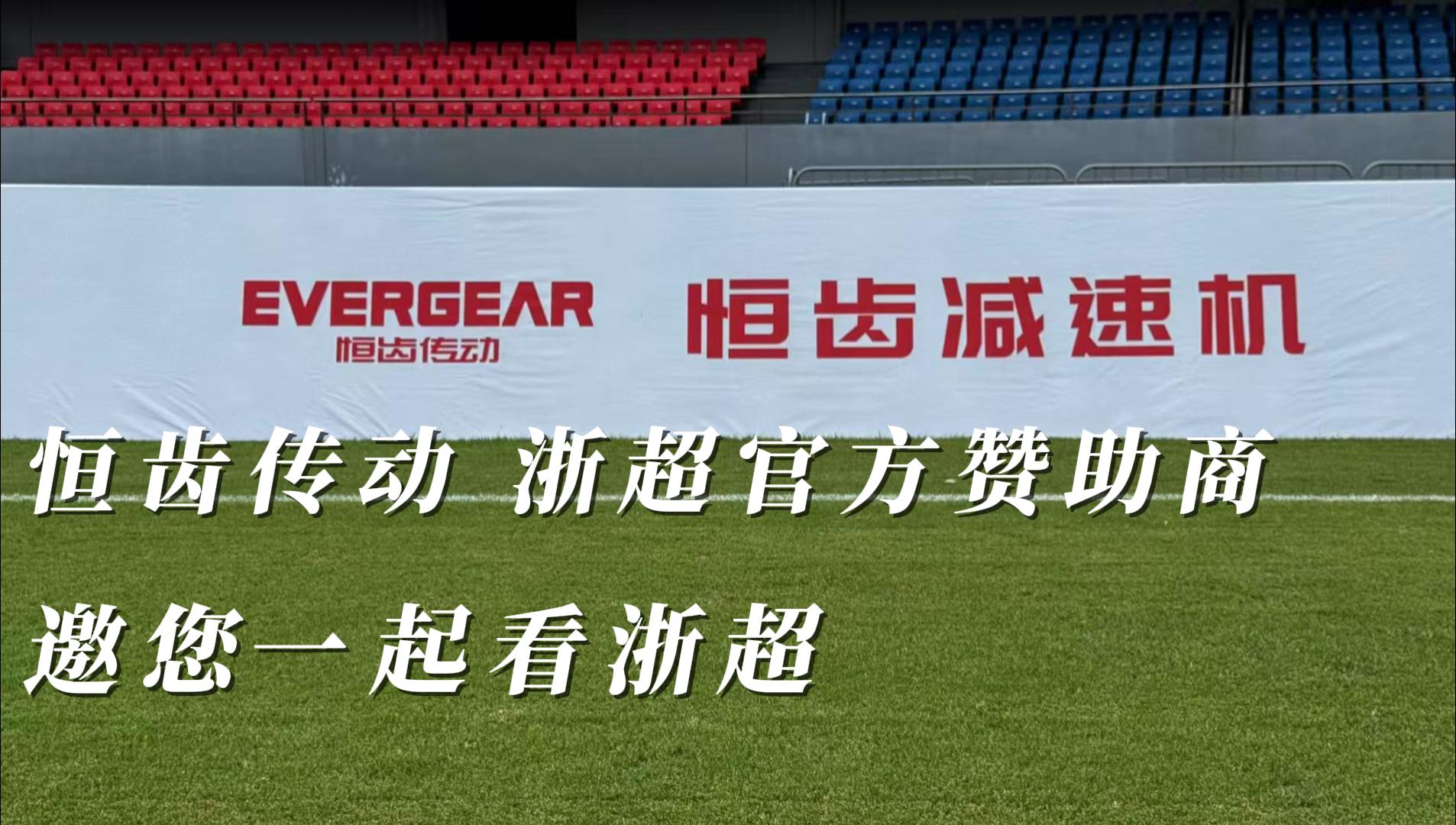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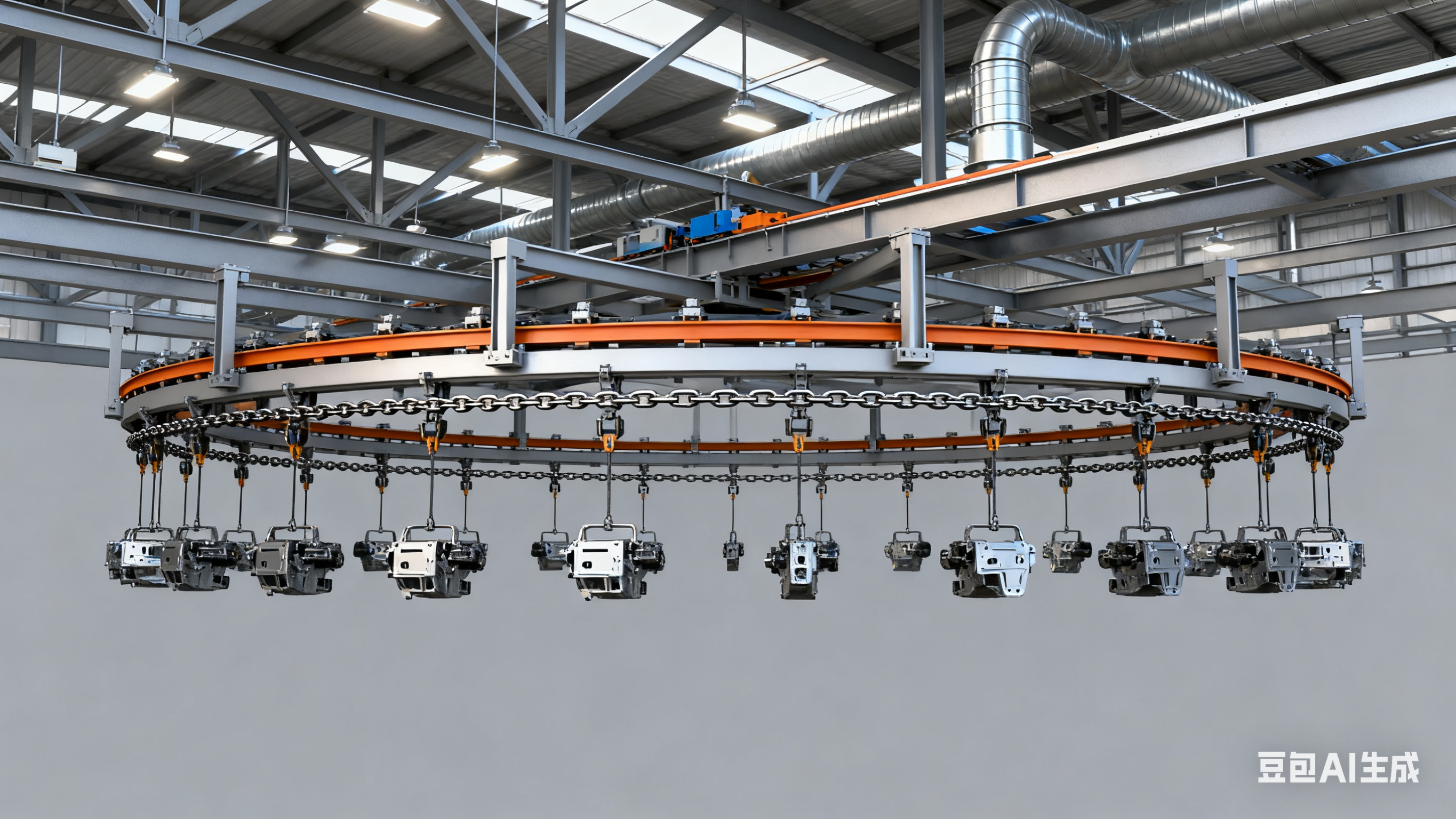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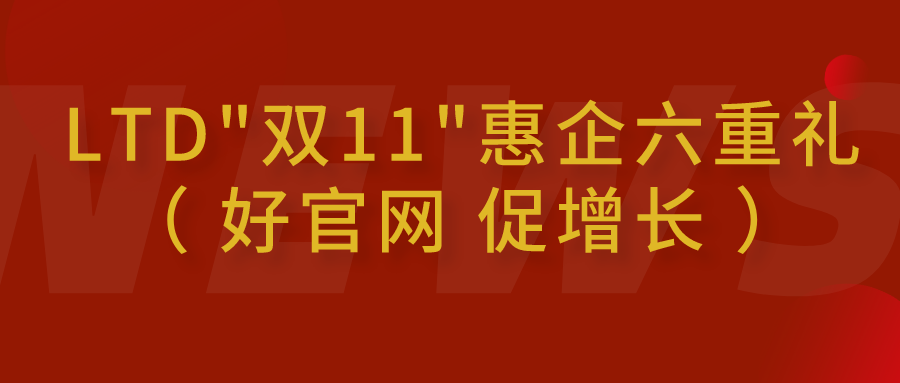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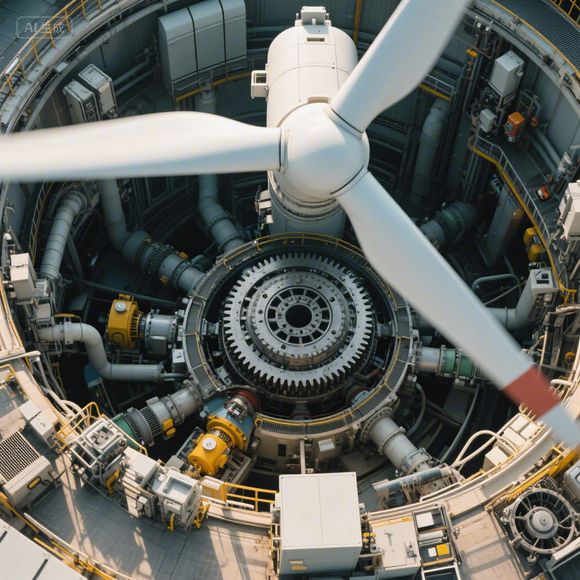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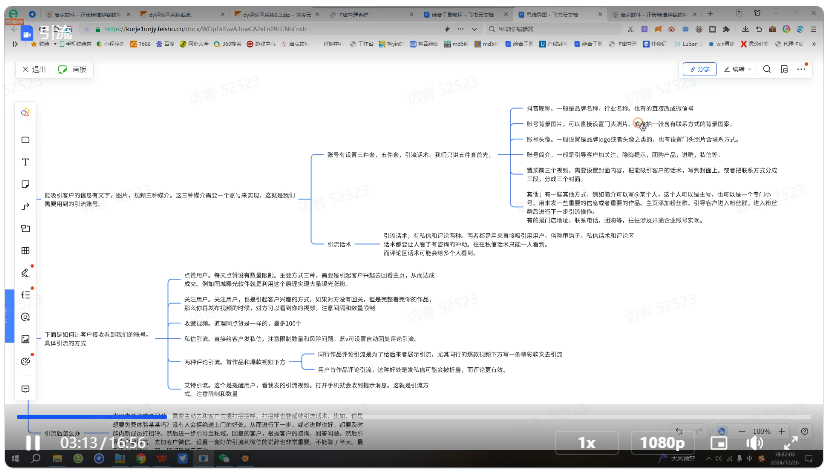



请先 登录后发表评论 ~